从北非、伊比利亚半岛、整个中东到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都能看到“坎儿井”(qanat)这种地下供水管道的身影。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但它们的作用都一样,那就是将泉水、湖泊、河流和含水层的珍贵水源,引流到干旱平原的低洼田地中。 这些坎儿井由手工挖掘而成,并且需要例行的手工维护。它们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而且有许多至今仍在“服役”,为人们提供农田用水和饮用水。
在干旱地区种植粮食一直是项艰辛且充满风险的工作。 自从一万多年前,人类首次学会了如何种植作物后,生活在降水有限的土地上的农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为他们的犁沟提供足够的水。
在某些地区,远方的季节性降雨和高山融雪会令江河泛滥,产生的径流淹没农田。 数千年来,埃及尼罗河流域这样的洪水周而复始地发生,直到近代,泛滥的尼罗河被阿斯旺大坝“驯化”。 同样地,河流洪水泛滥也养育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的美索不达米亚农田。 在这两个地区,早期的工程师们建造了复杂的运河、河道和积水盆地,来规范和节约用水。
然而,在这些地区以及其他炎热干燥的土地上,运河、渠道和积水盆地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蒸发。 烈日暴晒,令地表水以无情的速度耗竭掉。 因为水资源如此稀少且珍贵,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巧妙但较为耗费劳力的解决方案:将水引入地下隧道中以避免日晒蒸发,同时将这个地下隧道设计出坡度,让水在引力的作用下从源头流入干渴的农田。
究竟是谁挖的第一口坎儿井,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坎儿井可能起源于今天的亚美尼亚高原或者阿曼山脉,但最广为接受的假设是,在公元前1000年早期,坎儿井起源于今天通常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地区——伊朗西北部以及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地区,人们在这里的山区发现了地下水系统。 当时,古代的矿工也在这些山区开矿,他们应该掌握了很多建造隧道的知识。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地理学家兼早期水系统研究员戴尔·莱特富特(Dale Lightfoot)断言,关于这些灌溉系统的技术知识正是从这里向东、西方传播的,传播到了今天大约35个国家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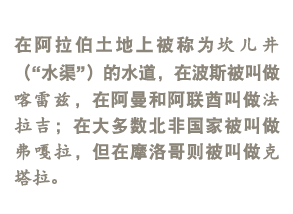 在今天的伊朗和整个中亚,人们通常以其波斯原名“喀雷兹”(karez或kariz),来称呼这种水资源管理系统。这个词实际是一个建筑学术语,意思是汇入更大地下水渠的小型进水道。 在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喀雷兹被称为qanat(中文称为“坎儿井”),这个阿拉伯语词意为“水渠”,已成为这类灌溉水道网络最常见的通称; 在阿曼和阿联酋,这个词叫做法拉吉(falaj),意思是“分割”和“安排”。 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大多数北非国家,它通常被称为弗嘎拉(foggara),但在摩洛哥则被叫做克塔拉(khettara)。 这项技术传播区域的最东端,即中国西北地区,突厥语系的维吾尔族人以其原来的名字“喀雷兹”来称呼它们,由此可见它们经由丝绸之路而传过来的波斯血统。
在今天的伊朗和整个中亚,人们通常以其波斯原名“喀雷兹”(karez或kariz),来称呼这种水资源管理系统。这个词实际是一个建筑学术语,意思是汇入更大地下水渠的小型进水道。 在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喀雷兹被称为qanat(中文称为“坎儿井”),这个阿拉伯语词意为“水渠”,已成为这类灌溉水道网络最常见的通称; 在阿曼和阿联酋,这个词叫做法拉吉(falaj),意思是“分割”和“安排”。 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大多数北非国家,它通常被称为弗嘎拉(foggara),但在摩洛哥则被叫做克塔拉(khettara)。 这项技术传播区域的最东端,即中国西北地区,突厥语系的维吾尔族人以其原来的名字“喀雷兹”来称呼它们,由此可见它们经由丝绸之路而传过来的波斯血统。
在伊朗,大多数喀雷兹绵延5至10公里(3至6英里),但有些会超过70公里(44英里)。 现在还在继续为人们服务的喀雷兹大约还有20000口之多,总长度大约275000公里(171000英里), 其中很多分布在广袤的伊朗高原上。伊朗高原西至扎格罗斯山脉,东至印度河流域,绵延大约2000公里(1250英里),每年平均降雨量大约只有15至25厘米(6至10英寸)。 直到20世纪中叶,伊朗四分之三的用水都是靠喀雷兹供应的。
在所有地方,坎儿井隧道的横截面通常都为1.5米(5英尺)高,1米多宽,刚好够用手工挖掘和维护。 竖井通常间隔大约50至100米(164至330英尺),与含水隧道相连,深度在10米至100米(32至330英尺)。
现代坎儿井的构造与古代的非常相似: 由专业挖掘师——在阿拉伯语中称为“穆卡尼”(muqanni)先挖掘竖井,然后用桶将掘出的泥土和岩石拖到地面上。 如果运气好,挖到大约15米(50英尺)深就能找到湿土或水源,但如果运气不好,就必须继续向下挖。 最后开始挖掘横向水道,斜度由测量员确定。
有时遇到土质不稳定的情况,穆卡尼可能会用瓦石加固井道和坑道。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穆卡尼在下井之前要做祈祷,这是传统。如果他们因为任何原因觉得这样做不吉利,他们会拒绝进入地下井道。
一份在亚述找到的文字记录,将最早建造坎儿井的时间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 据记载,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出征波斯期间,在西北方的乌尔米耶湖附近发现了一个地下供水系统。 萨尔贡的儿子森纳赫里布(公元前七世纪执政)采用波斯技术,在他的首都尼尼微附近和阿贝拉市内修建喀雷兹。
公元前525年,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征服了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数年之后,波斯王大流士一世要求卡里安希腊探险家西拉克斯(Scylax of Caryanda)建造一个绵延160公里(100英里)的喀雷兹系统,从西边的尼罗河河谷穿过利比亚沙漠到达哈里杰绿洲,其中哈里杰绿洲是利润丰厚的商贸路线darb al-arba‘in(意为“四十天路”)的主要站点之一。 已故学者伍尔夫(H.E. Wulff)于1968年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指出,“残存的坎儿井还在使用”,他推测这种技术“很可能与埃及人对他们的征服者表示友好,并向大流士赠与法老称号有一定的关系”。
后来,贸易和征服充当了坎儿井技术向东西方传播的催化剂。 在发现他们最拿手的导水沟渠建造技术与被征服的土地确实“水土不服”之后,罗马的土木工程师开始在这些地方建造坎儿井。 例如,约旦境内的“加大拉水渠”(Gadara Aqueduct)是大约十年前出土的罗马建造结构,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水渠”,而是地下水道——坎儿井。这个坎儿井系统全长170公里(105英里),是此类古隧道中最长的。 加大拉系统,也被称为qanat firaun或“法老的坎儿井”(Pharaoh’s Qanat),是在大约公元130年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一次访问之后建造的,部分路段沿用了早前的希腊式隧道路线。 罗马的这个版本虽然有部分已投入使用,但却一直没有完工。
北非最早的坎儿井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 考古学家和其他专家追查这项技术的迁移路线,发现是从埃及传到利比亚西南部加拉曼特人居住的费赞地区,然后从这个地区向东传播,穿过整个撒哈拉到了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在阿尔及利亚的绿洲中,坎儿井(在这里被称为弗嘎拉)促进了旨在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贸易关系的南北新商路的发展。 牛津大学研究中西部撒哈拉弗嘎拉的考古学家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说,绿洲是“今伊朗之外弗嘎拉发育程度最高的地区”。 威尔逊指出,虽然传统学术研究认为建造弗嘎拉的时间只能追溯到公元11世纪,但鉴于阿尔及利亚弗嘎拉和利比亚加拉曼特的弗嘎拉“在构造和命名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可能“有理由认为这个时间可以前推至公元7世纪或更早”。
提米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古拉拉沙漠地区的一个小绿洲城镇。该地以其赭红色的建筑和大量仍被用于灌溉椰枣等农作物的弗嘎拉系统而闻名。 2001年的最新正式统计结果表明,这里有大约250口弗嘎拉,但由于当地农民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电机井,弗嘎拉正在慢慢干涸。 电机井耗尽含水层的水源,而且与弗嘎拉不同的是,电机井可以不断向下钻。 阿尔及利亚各地都在上演这一幕,联合国关于那里的水资源调查指出,不久前还有1400口在用的弗嘎拉,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900口。 虽然最近相关方面已经在努力修复一些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还没传播到这里时就建成的弗嘎拉,但越来越多农民为现实所迫,正在改用更为现代的供水方法。
公元七、八世纪,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明向西方扩张,穿过北非,北进穿过地中海,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导致了加拉曼特时期之后坎儿井技术的第二次大传播。 从地中海东边的塞浦路斯到西边的加那利群岛,都在修建坎儿井。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地理学家保罗·沃德·英格利(Paul Ward English)指出,坎儿井也蔓延到了新世界,伴随着西班牙在墨西哥攻城的步伐,在Parrás、瓦斯特卡峡谷(Canyon Huasteca)、Tecamenchalco和特瓦坎(Tehuacán)留下了它们的踪迹。
在另一个方向,坎儿井传播区域的最东端,英格利观察到伊朗的坎儿井传播到了阿富汗、中亚丝绸之路上的绿洲聚居地,然后进入中国西部,“不过无法确定这次传播是发生在阿契美尼德还是其后的波斯王朝统治时期”。
新疆的绿洲城市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从西方到东方贸易路线的一个主要站点。 这座城市被群山环抱,但海拔低于海平面,座落在世界最深的内陆盆地之一吐鲁番盆地之中。 这种地貌为利用重力驱动流域径流进入地下输水隧道创造了理想的条件。
吐鲁番夏季炎热,干燥的风携带来附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 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开始,坎儿井就已经在为当地居民和过路的商队供水了。 从19世纪开始,吐鲁番的坎儿井水管理系统更是呈现增长之势,这在全球所有使用坎儿井的区域中可谓独一无二。
1845年,被视为中国德治楷模的中国著名官员和学者林则徐,做了英国两次成功入侵中国沿海的替罪羊,被放逐到遥远的新疆。 在西北生活的日子里,林则徐渐渐熟悉了坎儿井技术,推动这个技术传播到吐鲁番以外的地区,当时此举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到1944年,吐鲁番地区已经修建了大约379个坎儿井。到1952年,这个盆地里已建造了800个地下水系统, 累计总长度达到2500公里(1555英里),相当于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航道京杭大运河的长度。 今天,这个总距离已增加了一倍,而吐鲁番盆地里的坎儿井系统数量已超过1000个。
从伊比利亚到中国,很多干旱地区之所以能实施农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坎儿井。事实上,这些地方文明的诞生也要归功于坎儿井。 正如伍尔夫在1968年总结的那样,“伊朗坎儿井的建造规模可以媲美罗马帝国的大规模水道。 罗马的水道现在只是一道历史奇观了”,然而坎儿井技术“在3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为人们服务,并且还在不断地扩张”。
虽然伊朗和北非的坎儿井数量都在下降,但是它们在当地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西北地区的坎儿井也是一样,而且其长度和数量都在增加。将珍贵的水资源安全地保护在地下免于日晒,这项技术的恒久价值不言自明。
 |
罗伯特·W·雷布宁(lebling@yahoo.com)是在沙特阿拉伯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作家、编辑和传播学专家。 他是《烈火之魂传奇: 吉恩和吉尼从阿拉伯到桑给巴尔岛》(Legends of the Fire Spirits:Jinn and Genies from Arabia to Zanzibar(I.B. Tauris出版公司,2010年及2014年)一书的作者。他还与唐娜·佩珀代(Donna Pepperdine)合著了《阿拉伯的天然救济》(Natural Remedies of Arabia)(斯泰西国际出版公司,2006年)一书。 同时他还是《沙特阿美世界》的定期撰稿人。 |
 |
乔治·斯坦梅茨(www.GeorgeSteinmetz.com)定期为《国家地理》和《GEO》杂志供稿已超过25年, 荣获无数的摄影奖项,其中包括世界新闻摄影的两个一等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