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当时10岁,我永远都忘不了。” 艾哈迈德·博格盯着沙特阿拉伯西部塔伊非上方高地上朦胧的沙漠景象。 “我们出发去艾卜哈的野营度假地,就在山上。 那时,那里甚至没有沥青路。 只有一片荒野,远离城镇。 黎明时分,父亲叫醒我们,大家一片惊慌。 ‘猴子!’他大喊道。 ‘快点,拿好所有东西!’ 我们把能抓的都抓在手里。 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大约一百只猴子。 它们偷水果、食品、任何东西。 后来,我们下到山谷去捡我们的东西:鞋子和玩具。 我是真的吓了一跳! 这就是我对这些动物感兴趣的原因。” 儿时的兴趣在长大后变成了职业。
今天的艾哈迈德·博格是沙特阿拉伯国家野生动植物研究中心(nwrc)的主任,是幼年时在穷乡僻壤吓了他一跳的攻击者——长鬃狒狒——的世界级权威。
 |
| 崎岖多石的沙捞越山脉为长鬃狒狒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 大约65%的长鬃狒狒为野生狒狒,但还有35%在城镇附近生活、觅食,包括路边,例如塔伊非以西的15号高速公路沿线。 |
不像东非狒狒、黄狒狒、熊狒狒和几内亚狒狒(这些狒狒都只存在于非洲),阿拉伯狒狒生活在红海两岸,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一直到一水之隔的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半干旱山区。 除了智人,它们是阿拉伯半岛唯一的本地灵长类动物。
阿拉伯狒狒需要能喝水的河面和能睡觉的岩石斜坡,悬崖也可以。 沙特阿拉伯的沙捞越山脉就符合上述条件:沿也门边界向北绵延大约800公里(500英里),和红海海岸平行的地方生活着大约350,000只狒狒。 这是一条狭窄的走廊: 沙捞越东部的沙漠有悬崖,但没有水,西部的海岸平原则只有水,没有悬崖。
博格的家乡塔伊非就在沙捞越山脉海拔1900米(6200英尺)处。 这里非常适合狒狒生长,并因此出名。 特别是西边的郊区,数百只狒狒在岩石斜坡上蹦蹦跳跳,在公园附近游荡,从开心的智人手中哄得一些剩饭菜。
博格驾车带我到阿哈达西北几公里外,在那里,通往麦加的15号高速公路出现一系列设计精准的急转弯,向下驶离峭壁。 开出来后,前面是雄壮的沙漠风光,两侧路肩的岩石和四车道公路上则有许多蹦蹦跳跳的长鬃狒狒,有雌有雄,有老有少,有时看起来就像在公路上跳舞。 路上有一块大标志牌,上面写着Mamnooa rami al-akl lil-haywanat(“不要朝动物扔食物”)。尽管如此,司机仍停下来朝车窗外扔水果、面包和剩饭菜,吸引了一群群不停尖叫、在车头和车顶上翻筋斗的长鬃狒狒。
 |
| 上图: 一家人站在路边观看嬉闹的狒狒。 下图: 从社会学角度看,长鬃狒狒的组织结构为omus(即“单雄单元”),例如这只雄狒狒的身边有四只雌狒狒。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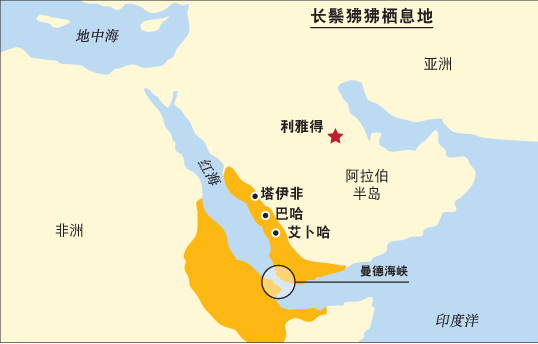 |
| 跨越红海 |
非洲狒狒怎么会出现在阿拉伯半岛? 还是阿拉伯半岛的狒狒跑到了非洲?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灵长类动物学家几十年。 汉斯·库默尔在他1995年出版的代表作In Quest of the Sacred Baboon(狒狒探秘)一书中写道:“这是个费解的问题。 长鬃狒狒肯定来自[红海]的一边或另一边。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到底是哪一边。”
红海两岸的其它哺乳动物彼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羚羊和豹子,非洲的种群和阿拉伯的种群在生理和行为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但阿拉伯狒狒则基本相同。 这表明它们曾长期与世隔绝,逐渐进化成现在的样子,只是在最近才散布到其它地方。
库默尔更倾向于非洲起源论,他提出一个有趣的想法,即狒狒是由古代埃及人从海的另一边运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埃及人崇拜这种动物。 (根据记录,公元前1500年左右,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派人远征“邦特地区”,大概是现在的非洲之角,他们带回了活的长鬃狒狒。) 库默尔提出,红海的海上商贸崛起时,狒狒跳到船上,并因此在阿拉伯红海海港的山区安家落户。
如果他是对的,则非洲和阿拉伯的长鬃狒狒应当具有相同的基因。 但他的结论主要靠观察得出,那时DNA测试的应用范围还没有那么广。
在利雅得之外的哈立德国王野生动植物研究中心的实验室中,由英国遗传学家布鲁斯·维尼带领的研究团队于2004年宣称,阿拉伯狒狒的线粒体DNA (mtDNA)多样性表明,狒狒移居到阿拉伯肯定发生在20,000多年以前,比人类文明的出现还要早。
因此,狒狒是独立完成这段旅程的。 但这是怎么发生的? 它们是不是缓慢地从埃塞俄比亚向北进入埃及、穿过西奈沙漠后从北方进入阿拉伯? 如果是,则从遗传学上来看,现在最北边的狒狒族群应当比南边的狒狒族群更接近非洲狒狒。 但维尼的分析显示,厄立特里亚和塔伊非样本之间存在显著的遗传多样性,而这两处正好在红海两岸的最北边。
因此,科学家把眼光放在了南部。 曼德海峡在红海海口将也门和吉布提隔在两岸,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只有30公里(18英里)。 在冰川期,地球的海平面要低得多,因此,在过去的几十万年时间里,此处的海峡可能有若干次形成大陆桥,维尼和他的研究团队据此得出结论,狒狒可能是在130,000至440,000年之前从非洲迁移到阿拉伯的。
京都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小竹高吉与塔伊非的艾哈迈德·博格密切合作,他提出,在漫长进化过程的某个遥远的古代,狒狒的祖先跨过曼德海峡进入阿拉伯。 后来,经过成千上万年,这里的狒狒进化出阿拉伯本地独有的特点,然后又回到东非的群山中。 最近的分析发现非洲和阿拉伯狒狒之间存在的遗传差异似乎支持这种观点。 小竹的研究仍在准备阶段,因此,他的假设还没有经过测试,但它提出了一种比较有吸引力的可能性。 狒狒可能根本就不是非洲才有的动物,而是阿拉伯物种。 |
狒狒不是轻盈、苗条的树上居民: 它们身短、敦实且有力。 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达到30公斤(66磅),它那长长的吻张开时即可露出里面5厘米(1.5英寸)长的犬牙。 雄狒狒的双颊、双肩和上身都覆盖着银色的鬃毛,眉骨高高隆起,下面是一双犀利的眼睛,整个外观都透露着一种力量感。
雌狒狒只有雄狒狒的一半大小,身上覆盖着短短的棕色毛发,完全不像雄性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狒狒由雄性做主,它将雌性网罗在自己周围,实行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即“单雄单元”(又称omu),博格解释说。 在观察高速公路路肩上的狒狒时,
博格指出若干个omus: 一只雄狒狒一般能控制二至八只雌狒狒,加上它们的幼仔。 也有更大的群体,他解释说: 两个或三个omus在一起生活和觅食构成一个家族;两个或三个家族保持密切联系,构成一个部族,几个部族一起构成一个由一百甚至更多狒狒组成的狒狒群,它们每天都一起从睡眠场所前往觅食场所和休息场所,最后再一起返回睡眠场所。
每个群体的社会秩序都是一致意见和胁迫共同作用的产物: 我们经常会看到雄狒狒抓住雌狒狒的尾巴将它拖回,防止它离群。 博格补充说,这种行为和非洲雄狒狒的行为不同,后者通过决斗赢得雌狒狒。 “这是为了适应本地的干旱环境。 和决斗相比,看管好雌狒狒消耗的能量更少。 在这里,保持能量很重要。”
博格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在过去30年,他一直独自工作。 与非洲的种群相比,长鬃狒狒领域只发表了少量学术论文
 |
| 马修·特勒 |
| ”我们要阻止人们给狒狒喂食”,艾哈迈德·博格说(上)。 共食(即狒狒部分或完全靠人类食品生存)已经造成社会压力。 对于雌性来说(下),共食造成的饮食过度会缩短生育间隔,导致狒狒数量过度增加。 |
 |
。 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对自然界其它部分的了解不断加深,但对长鬃狒狒的了解似乎有些滞后。 瑞士灵长类动物学家汉斯·库默尔对此提出了一项假设。 作为狒狒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研究的是埃塞俄比亚狒狒。尽管多数哺乳动物都用人类无法察觉的气味或我们认为一点也不性感的声音吸引异性与之交配,他写道,狒狒却是视觉动物,它们展示身体和性能力的方式人类也可以理解。 更糟糕的是,他补充说,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半裸的: 雄性的鬃毛覆盖着它的上半身,但和雌性一样,它从腰部向下都是赤裸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看到狒狒会感到很尴尬。
在阿拉伯文化中,尽管hadith(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的话)曾提到狒狒,但丰富的传统诗歌中却不见狒狒的踪影,而其它许多野生动物,例如羚羊和瞪羚,甚至狼和不受欢迎的鬣狗都有提及。 艾哈迈德·博格(他本人就是文学家并发表了诗歌)一边笑一边讲了一个和库默尔极为相似的说法:“狒狒既没有漂亮的外表又不好吃”,他告诉我,“因此,诗人不屑于描写它们。”
这种不协调的关系一直存在。 沙特阿拉伯只有大约65%的狒狒是野生的,其余的都生活在城镇周围,特别是塔伊非,这里恰好也是沙特王国最受欢迎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这些狒狒属于共食动物,即它们和我们吃一样的食物,这表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人类食物为生。
博格将我带到塔伊非南侧的瓦迪利亚,那里包括狒狒栖息地的全部要素。 这里的山谷非常陡峭,有由岩石构成的悬崖,附近的小河谷和泉水一直流到大坝形成的湖泊中。 除了吃这里野生的洋槐果实和蓟罂粟多汁的根(Argemone mexicana),它们每天早晨还会步行一段不长的距离来到鲁达夫公园(本地的野餐区),并在公园工作人员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从垃圾箱里收集人类的剩饭菜,直到工作人员将他们赶走。
 |
| 由于食品很容易获得,狒狒的活动范围缩小,就像人类一样,运动不足的狒狒也出现了健康问题。 |
“长期以来,共食在这里已经成了问题”,博格告诉我。“而在过去30年,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高速发展比环境更重要。” 有4%的狒狒(大约有数千只)现在完全依赖人类的食品来源生存。
但是,正如阿哈达司机的行为所显示的,它们不只是靠主动袭击寻找食物: 人们在喂养狒狒。 “有些人认为猴子和猪是受神惩罚的人类,因为它们不遵守神的律法”,博格说。 “他们给这些动物喂食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奖励。”
他告诉我本地有一位知名人士,他每天收集镇内各餐馆和糕饼店的剩饭菜,用袋子装好并拿到阿哈达喂狒狒。 我驾车前往阿沙法,即塔伊非南部的山区游乐园和野餐场所,那里的游客从路边小摊上买水果,然后直接扔给等在那里的狒狒。
我问三位从盐部的沿海城市远道而来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其中一个人说。 “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是在做好事,这样能获得上帝垂爱”,另一个人说。
在一个阿沙法风景如画的观景高地上,眼前是一片异常美丽的森林峭壁和幽深沟壑,苏莱曼(和朋友胡麦德从北方城市海尔来此度周末)正在设置烧烤架。
“给狒狒喂食是祈祷和斋戒的组成部分”,他告诉我说。“这是件好事。它们没有其它东西可以吃。 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它们就不会来找我们,是不是?”
这种行为虽然是好意,但却是有生物误导性的干预行为,会产生严重后果。 野生长鬃狒狒的总数也许能达到120;但共食狒狒的数量则有可能超过800。由于寻找食物的需求不那么大,它们倾向于在7或8平方公里(3平方英里)的较小范围内游荡,不到野生族群活动范围的三分之一。
 |
| 马修·特勒 |
| 前往塔伊非的路上,标志牌上的内容翻译过来就是“不要扔食物给动物”。 |
这会导致拥挤,造成社会压力。 雄性发现自己无法维持规模日益变大的omus的秩序,“雌性”则不断出走,与其它雄性交配,这些雄性又反过来抢占更多的雌性。 阿哈达共食狒狒抓尾巴的行为实际上是压力引起的,博格说: 野生族群不会发生这种事。 喂养过度还缩短了生育间隔时间,导致族群拥挤。 然后还有垃圾食品问题,这些食品盐、糖和脂肪含量极高: 共食的长鬃狒狒出现了健康问题,包括肠道寄生虫发病率增加。
这个问题还威胁到人类,因为和狒狒比邻,人类得血吸虫病和结核病的风险增加。 狒狒们袭击塔伊非周围的农村,偷窃农作物和毁坏篱笆和其它建筑。 有一个狒狒群进入一处军事基地,它们扯烂了军用车辆上的座椅,还咬断了雷达缆线。 该地区的交通意外也有所增加,事故原因不只是因为公路上有动物: 2010年的阿拉伯新闻报道了一起事件,狒狒向一辆卡车扔石块,导致一名塔伊非男子死亡。
博格说这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狒狒和人类比邻而居。 他很清楚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森林砍伐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栖息地分割,加上猎人对狒狒传统猎食者狼、豹子和鬣狗的捕杀。
在博格的指导下,nwrc正试图解决共食问题,保持狒狒的野生状态。 20世纪90年代末,该组织在艾卜哈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将狒狒数量减少了一半: 科学家用“人道扑杀”的方法,加上输精管切除术和荷尔蒙植入降低狒狒的出生率,同时官方开始部署公共标志,并允许警察向路边喂食行为征收罚款。 在控制狒狒繁殖的同时纠正人类的行为很关键。
| 来自天堂的类人猿? |
长鬃狒狒在古埃及备受尊崇。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新王朝时期,人们从努比亚(今天的苏丹和邦特,可能是红海南岸地区)进口狒狒,用于宗教仪式。 我们还不清楚它们在埃及宗教中的确切地位,但它们似乎被视为神祗降临的媒介和人类的代理: 有许多绘画场景描述狒狒在建造船只和参与收割,狒狒还有可能被做成木乃伊,在王室成员的轮回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
人们通常将长鬃狒狒与透特联系在一起,他是众神的信使,知识的源泉(透特被描述为名为阿恩的类人猿),是平衡之神,通过根据宇宙动力源称量死者的心脏寻求平衡。 古埃及绘画和雕塑中的长鬃狒狒比比皆是,一般都摆出崇拜太阳的姿势,作者假设其源自雄狒狒梳理毛发时采用的姿势: 头向后仰,手臂举起伸向天空。 |
“如果不采取这样的一揽子方案,我们就无法取得成功”,博格解释说。 “简单地消灭狒狒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它野生族群会搬来填补空缺成为新的共食族群。 我们必须阻止人们给它们喂食。 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开展公共宣传活动。”
为此,nwrc开始为高中的环保教育课提供资金,并成立了新的游客中心。 博格正在组织召开研讨会,向塔伊非的政府官员简要介绍狒狒共食引发的问题,找出环境原因并提供指导,制定可持续解决方案。 去年八月,他出席了某个全球性会议,会议介绍了香港为控制附近的猕猴种群采取的避孕和立法干预措施及其重大成果,这是一项长期性计划。 博格计划在沙特阿拉伯也采取同样的措施,目前正等待塔伊非政府批准。 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回头再看看阿哈达,车辆挤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7、8辆车一字排开,乘客们逗弄着嘴里塞满食物的小狒狒,威严的银发雄狒狒则在一边盯着。 一名穿着橙色连身衣的市政工人孤单地收集着地上的塑料瓶和食品包装袋。
这种场景一点也不新鲜。 自古以来,往来于塔伊非和麦加之间的商人和旅客都要经过阿哈达,悬崖上古老的岩石小路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并存。 学者雅谷特·阿尔·哈马维描述了1228年的阿哈达,他在Mu’jam Al Buldan(国家字典)一书中平淡地描述了这里居住的狒狒。 同样的,互联网搜索可以找到大量有关狒狒滑稽动作视频的夸张评论。 “我住在塔伊非”,瓦利德·吉拉尼写道。 “每次去麦加或吉达,这些狒狒都会给我们制造困难…… 有时我们不得不改道。”
在正式的阿拉伯语中,狒狒被称为qurud。 这个词隐含有守财奴或生活贫困的意思,源自另一个含义为“不幸”的词。 但在流行语言中,多数人都知道,hamadryas(狒狒)不是指sa’dan(翻译过来就是“幸福的人”),就是指rubah,即“得利者”。 我们看着狒狒从阿哈达的好心人手中取食,旁边就是清甜的山泉,晚上还可以在岩石峭壁上安全地休息,它们正像守财奴一样在幸福地兑现它们的利益,不管未来有多不确定。
| 狒狒会不会养宠物? |
2011年,YouTube上贴出了一段视频,内容是塔伊非的长鬃狒狒将野生小狗据为己有,并作为宠物养大。 事实证明,这段视频极受欢迎,吸引了600,000多名观众。 这段三分钟的视频摘自“像我们一样的动物”,这是一部描述动物行为的电视系列片,曾获得许多奖项,由法国的一个团队和国家地理频道合作制作。 YouTube上的这段剪辑描述的是一只雄狒狒抓住一只小狗的尾巴,戳它并在尘土中拖动它;镜头转到成年犬和狒狒身上,它们显得很放松,解说员解说道:“被绑架的小狗在狒狒的家庭中长大,它们一起吃、一起睡。” 相互照顾的场景慢慢淡出,温情的音乐弥漫。
人们早就知道绑架是狒狒的正常行为: 雄狒狒会尝试将小狒狒从正在哺乳的雌狒狒身边抢走,以此加强它们在族群中的地位。 但为什么狒狒会绑架其它物种? 抛开这些煽情的音乐和旁白以及精心编辑的视觉效果,这段视频剪辑否真的表明狒狒试图将狗作为同伴,而狗也将狒狒视为主人,还是人类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了视频中?
共生在自然界中很普遍。 但养宠物,即其中一个物种在没有明显功能性原因的情况下收养另一个物种并负责它的终身喂养和护理,却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 除了捕捉猎物,已知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智人。 著名的大猩猩科科养了一只猫,一只肯尼亚河马和一只巨大的乌龟成了朋友,还有一些例子,但都发生在人工环境中。 在野生世界,我们曾观察到西非的大猩猩在抓住一种像小老鼠一样的哺乳动物蹄兔后,会养一段时间用来玩耍,但最后都会毫无例外地将其杀掉,用作食物。
为此,YouTube上的剪辑吸引了哈尔·赫尔佐格,他是西卡罗莱纳大学人类与动物互动方面的专家。 他在今日心理学和赫芬顿邮报上开辟专栏,整理了很多观点,探索塔伊非狒狒饲养狗作为宠物的可能性。他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并对视频上的内容提出了许多问题:
- 狗和狒狒在一起生活多长时间?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
- 狒狒除了宠爱狗,和狗一起玩耍外,是否还从狗那里得到别的任何东西?狗会获得哪些好处?
- 狒狒是否曾杀死或吃掉小狗?
但到目前为止,答案仍然很不确切。 约翰·威尔斯是沙特阿拉伯美国狒狒研究协会的联合创始人,这是小型志愿者组织,总部设在吉达,他们对这部视频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 “我也持怀疑态度”,他告诉我,“我希望能看到没有编辑的脚本。”
不管怎样,威尔斯都认为视频的内容无疑是很不寻常的,他解释说他见过狒狒照顾猫。 “在阿沙法,我亲眼见到四只雌狒狒从岩石斜坡上下来,跑到一只喵喵叫的小猫跟前。 小猫立即停止发出叫声,并开始在它们身上挨挨擦擦。 这是一种调皮的行为,在周围蹦蹦跳跳。 然后,我看到雄狒狒也跑下斜坡,带着小猫一起去喝水”。
在他的Some We Love, Some We Hate, Some We Eat(为什么有些是宠物,有些是食物)一书中,赫尔佐格宣称,养宠物者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即社会模仿和同类认可。 压力很大、过于拥挤的栖息地和食物过量是不是造成塔伊非共食狒狒饲养宠物、寻求安慰的原因? 这些动物是否形成了护理文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猜测。 |
欢迎各位对译文提出反馈意见
我们欢迎读者对译文发表意见,这样能帮我们的语言工作者提高翻译质量。请将意见用电邮发送到saworld@aramcoservices.com,主题栏请用英文标明“Translations feedback”。由于收到的意见量大,我们可能无法回复全部邮件。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