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卡洛琳·斯通 |
| 上图中克什米尔匣子的细部以水仙花为饰,采用莫卧儿风格绘制而成。 |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番红花、郁金香、水仙花、风信子以及其他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无数种花朵,北欧或者美国大多数地区的春季会是怎样。 这几乎等同于欧洲菜肴中缺少了美洲的水果和蔬菜:土豆、玉米、辣椒、西红柿和南瓜——更不必说巧克力、菠萝和香草了。
 |
| 左图: 莱顿州立大学图书馆/维尔纳·福尔曼档案馆/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右图: 画册/艺术资源 |
| 藏红花(番红花)大概在十三世纪引入欧洲,很久之前就表现出了药用价值,以及更重要的经济价值。 左图为十世纪阿拉伯版迪奥科里斯《药物论》(De Materia Medica)中对番红花的记载,而右图为十五世纪的插图,描绘了一名妇女采集藏红花花粉的场景。 |
自古以来,植物一直在不断迁移以及被人移植;但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伊斯兰时期,人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在经济或药用方面有重要价值的植物。 在十六世纪之前,人们不太看重纯作装饰用的花朵,不过他们认为有香味的花朵有益于健康,并因此将其归为草药。
卡托的《论农业》(On Agriculture)撰于大约公元前160年,其中安达卢斯和中世纪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植物学家的农学作品等论著,主要针对这些类别花朵进行研究。 就连伊本·巴萨尔(Ibn Bassal)也很少因美丽或罕见提及某种花朵,虽然他在十一世纪后期从哈吉返回西班牙的途中收集了大量植物,并编纂成收录180多种植物的《农业全书》(Diwan al-Filaha)一书。 这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他曾先后担任托莱多和塞维利亚皇家植物园的主管。
 |
| SNARK/艺术资源 |
| 这幅微型画可追溯到1430年左右,是赫拉特学校的一名画师所作,描绘了一处种植有大量蜀葵的皇家花园;图中的蜀葵在中亚地区特别常见,在十三世纪左右传入北欧。 |
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波植物引种发生在古典时期。 例如,有史料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四世纪发动的波斯战争中将柠檬和桃子带到了欧洲。 其他柑橘类水果(尤其是香橼)都是在地中海周围发现的,且几乎都是酸橙(也称“塞维利亚”橙)。 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陨落后,农业逐渐衰退,许多植物(包括香橼)都是在八世纪穆斯林教徒进入欧洲时被引入或重新引入的。
另一波植物引种发生在十字军东征时期。 实用价值又一次被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英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在1580年代写到了植物引种的价值,讲述了一名朝圣者如何混在同伴中将藏红花(番红花)花茎偷带回英格兰,冒着生命危险“为自己的祖国做贡献”,与公元六世纪僧侣们冒险将蚕茧从中国偷运到拜占庭的故事不谋而合。
如今在春季里遍布北欧花园的藏红花,大约是十三世纪中期引入英格兰的。 它的名称源于阿拉姆语的kurkama,原产地是地中海和欧亚大陆。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番红花是在克里特岛培植的,因为它在这里至少有3,000年的种植史。 藏红花可用作香料、药物和染料,价值很高,因此几乎每部关于质量控制的法典中都制定了反掺假规则。 番红花的意义并不在于其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其作为经济作物的价值。
大概在十三世纪中期传到英格兰的另一种植物是蜀葵。 这种植物原产于欧亚大陆,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乡间花园的代名词。 其中大量品种来源于中亚,并且常出现在许多微型绘画中,尤其是十五世纪中期赫拉特学校的绘画中。 (参阅上方插图。) 它来自巴勒斯坦,因此人们认为其名称源自“Holy Hoc”(即“神圣的锦葵”)。 与同属中的许多植物(包括药用蜀葵,以及大众喜爱的埃及和突尼斯蔬菜长蒴黄麻)类似,蜀葵具有药用价值,这大概是它被引入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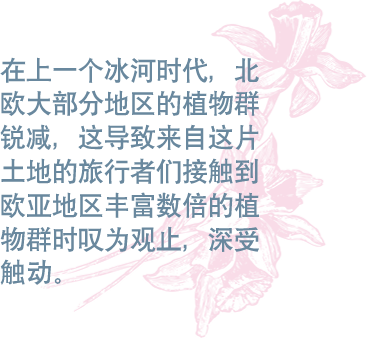 英格兰有自己土生土长的蔷薇——犬蔷薇,不过在十三世纪,外观美丽且芳香四溢的突厥蔷薇传到了英格兰海岸,来源地则可能是几世纪以来一直将其作为重要经济作物的叙利亚。 叙利亚自然学家阿勒迪马什基(al-Dimashqi)在1300年左右撰写的著作中,纯粹从经济方面讨论了突厥蔷薇作为“著名的大马士革玫瑰水”关键原料的意义。
英格兰有自己土生土长的蔷薇——犬蔷薇,不过在十三世纪,外观美丽且芳香四溢的突厥蔷薇传到了英格兰海岸,来源地则可能是几世纪以来一直将其作为重要经济作物的叙利亚。 叙利亚自然学家阿勒迪马什基(al-Dimashqi)在1300年左右撰写的著作中,纯粹从经济方面讨论了突厥蔷薇作为“著名的大马士革玫瑰水”关键原料的意义。
装饰性植物品种的增加,要归功于远东地区的园艺师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实行选择育种。 到1500年左右,他们的这种态度似乎也向西渗透到了穆斯林世界和欧洲。 巴卑尔(Babur)是十六世纪初期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创立者,也是充满激情的大自然爱好者和花园创造者,他极其喜爱郁金香。 1504年到1505年,他在喀布尔地区(位于多种郁金香属生长地的中心)写道:
 |
| 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
| 一朵具有象征性的郁金香,装饰在伊斯坦布尔鲁斯坦帕夏清真寺(1563年建成)的砖瓦上。 由于许多品种起源于中亚,郁金香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受欢迎的花朵和艺术图案之一。 |
色彩缤纷的郁金香布满了眼前的山麓;我曾经一一数过,结果数出了32或33个不同的种类。 我们将某种香味有点像红玫瑰的郁金香命名为“玫瑰香”,这是一种只在谢赫平原上自然生长的郁金香。 这里还有一种“百叶”郁金香;它也是自然生长,多见于古尔外滩狭窄地带的出口(位于帕尔旺下方的山边)。
后来,巴卑尔不断尝试将家乡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克什米尔的多种郁金香移植到印度。 其中的某些品种常出现在莫卧儿微型画中,也常作为刺绣、纺织品、地毯和家具以及雕刻和镶嵌中的装饰图案。
人们对种类繁多的郁金香的热爱渐渐向西传播,影响了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当地人在十六世纪对花朵和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郁金香、风信子、玫瑰和康乃馨是人们的最爱,而水仙花和桃花也深受人们喜爱。 郁金香反复出现在无数砖瓦上,出现在来自伊兹尼克的著名陶瓷制品上、宫殿的装饰绘画上、手稿的漆制封皮上以及纺织品(从丝绒到刺绣棉布围巾)上。 在阿尔巴尼亚都拉斯,于十八世纪Lâle Devri(郁金香时期)鼎盛时期兴建的一座清真寺上(最近刚刚完成修葺),从塔底到塔尖甚至都装饰有郁金香。
 |
| 大英图书馆 |
| 此页绘于1630年代,是为了纪念莫卧儿王子达拉·旭珂(Dara Shikoh)所制。图中精心描绘了中亚和克什米尔的一些花朵,其中包括另外几种引入欧洲的花朵:玫瑰、鸢尾花、飞燕草和像是亚洲金盏花的植物。 |
十七世纪的奥斯曼旅行家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Çelebi)描述了土耳其的园艺家公会,并多次提及花朵及其用途。 例如,人们会将有香味的花朵放在清真寺内,并用大托盘盛满花朵,由哈吉商队从伊斯坦布尔传入麦加。 他还描述了苏莱曼一世宫殿中的埃迪尔内花园: 它们是“地球上其他任何花园都比不上的,甚至连日耳曼帝国的维也纳皇宫花园也无法与之相比。” 花园中种植的花朵包括“中国风信子”。
虽然在十八世纪中期之前,花朵从中国到西方的大批移植尚未开始,但是一篇名为《节日的好处》(Tuhfe-i Çerağan)的论著(十八世纪初期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所著),描述了提着灯火在夜间赏花的节日习俗,如何随着从中国返回的大使传到了西方。
不过,关于各类花朵的信息主要是来源于精美的插图论著。其中,最好的论著典范保存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的图书馆中。 例如,可追溯到约1736年的《风信子图集》(Sümbülname)用插图说明了42个品种。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根据它们的名称判断,其中有一两种是从荷兰移植回奥斯曼世界的。) 其他一些图册详细介绍了花朵的起源和花朵的培育,也常有介绍关于主要植物育种家和收藏家的注释,以及有名花茎的名称和所有者,甚至还列出了价格。
“水仙花起源于阿尔及利亚。 在这片土地上首次播种水仙花的人是艾哈迈德·瑟勒比(Ahmed Çelebi)。”阿布杜拉·埃芬迪(Abdullah Efendi)在《Sükûfenamesi》(十七世纪关于水仙花的论著)中写道。 他继续描述了水仙花的品种和培育,并展示了数十种水仙花的图片。 和他相比,之前的作者仅提供了粗略的信息。 例如,波斯旅行家纳斯尔·呼斯刺(Nasr-i Khusraw)在记述他在1047年沿海路从哈马到大马士革的旅行时,写道“我们来到一片平原,这里铺满了盛开的水仙花,整个平原宛如一片白色的花海。”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 此外,尽管西班牙汇聚了种类繁多的水仙花,但伊本·巴萨尔仅提到了这里的“白色水仙花”、“黄色水仙花”和“长寿花”。
 英格兰有自己土生土长的野生水仙花(Narcissus pseudonarcissus),它们因华兹华斯(Wordsworth)闻名于世;不过到十六世纪之前,园艺家们一直在寻找新品种。 著名的园艺师约翰·特雷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在自己的某本植物名录中写道:
英格兰有自己土生土长的野生水仙花(Narcissus pseudonarcissus),它们因华兹华斯(Wordsworth)闻名于世;不过到十六世纪之前,园艺家们一直在寻找新品种。 著名的园艺师约翰·特雷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在自己的某本植物名录中写道:
1630 年从外国获得。 来自君士坦丁堡彼得·威奇爵士(Sr Peter Wyche)[英国大使]:
……关于水仙
关于仙客来属
4种毛茛属
咖啡色郁金香属
深紫色郁金香属
4类海葵……
 |
| 卡洛琳·斯通 |
| 郁金香花和郁金香图案的流行风潮从土耳向西方和北方蔓延。 位于阿尔巴尼亚都拉斯的这座十八世纪尖塔饰有郁金香图案。 |
两年后,他获得了风信子、郁金香和几种水仙花,其中包括可能属于多花水仙(纳斯尔·呼斯刺赞赏的品种)的“君士坦丁堡水仙”。
虽然介绍康乃馨和其他花朵的书籍也存在,但是至今为止,介绍玫瑰以及郁金香的书籍最常见。 根据十八世纪的某本论著,苏莱曼一世手下的首席法官埃布苏德·埃芬迪(Ebüssuud Efendi)对郁金香的流行起着关键作用。 举例来说,他得到某种白色郁金香(可能是土耳其博卢地区的野生郁金香自然突变而成)之后,在自家花园中播下了种子。
另一本由芬尼·瑟勒比(Fenni Çelebi)撰写的论著《Sükûfenamesi》,提供了关于“克里特岛郁金香”的详细信息。这种郁金香可能是穆罕默德阿加(Mehmed Aga),在长达21年的克里特岛干地亚攻城战(史上最长的攻城战)期间收集和传播的。 由威尼斯人统治的这座城市最终在1669年败给了奥斯曼军队,至此他才能够将收集的花朵安全带回伊斯坦布尔。
到十六世纪,对新花朵品种和外国花朵品种的喜爱已深深植根于欧洲社会,此时人们开始为了审美爱好积极搜寻郁金香等花朵,不再局限于花朵的实用性。
 |
| 克里斯蒂的图片/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
| 十七世纪德国《友谊画册》(Album Amicorum)中的一幅插图,其中可以看到一系列从东方引进的花朵,其中包括郁金香、鸢尾花、贝母、野生剑兰等。 |
关于郁金香名称的由来以及传到欧洲的方式,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 1546年,法国自然学家埃尔·贝龙(Pierre Belon)开始自己的科学之旅,游历了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并在1553年发表了自己的观察结果。 他评论道,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在头巾(又称tülbend)上饰有郁金香是一种时尚,其中“tülbend”与郁金香一词依稀相似。 由于郁金香的土耳其语为lâle,因此人们认为郁金香的现代英语名称是混淆使用了这种花朵的头巾装饰一词的结果。
但没有证据表明,是贝龙将郁金香花茎带了回来。 有种看似合理的理论认为,奥地利外交家奥吉尔·吉斯兰·德·巴斯拜克(Ogier Ghislain de Busbecq)将一些郁金香赠送给了自己的好友,也就是当时负责维也纳皇家药用花园的佛兰德植物学家卡罗卢斯·克卢修斯(Carolus Clusius)。 德·巴斯拜克是苏莱曼一世王朝的大使,他在1554年到1562年期间每年都要在伊斯坦布尔住上一段时间。 有史料认为,除了郁金香以外,他还将许多其他花茎和植物(包括丁香、麝香兰和悬铃树)带回了家乡,送给了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朋友。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克卢修斯搬到了莱顿,正是在这里他建立了欧洲最早的艺术植物园之一。 因为这些传播,荷兰在1630年代涌现了“郁金香热”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成就了今天数以百万美元的出口行业。
 |
| 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
| 这幅微型画展示了几个欧洲人与两个土耳其人在花园中用餐的情景。 这种场合可能会赠送鲜花、种子或花茎等礼物,也可能会推荐这些礼物的购买地。 |
不过,对花茎的大量需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2002年《苏丹的花园》(A Garden for the Sultan)一书中,努尔汗·阿塔索伊(Nurhan Atasoy)引用了托卡比的账目,其中有一例是1592年曾紧急请求从土耳其中南部马拉什的夏季牧场运送50,000朵白色和50,000朵蓝色风信子。
在花园花朵传回欧洲的过程中,外交官和商人起着重要作用。 他们可以接触到各类人群,其中包括植物收集者、花园主人及标本获取地的知情者。 克卢修斯提到,他见证了1575年维也纳第一株绵枣儿(西伯利亚绵枣儿)从花茎逐渐成长直至盛开的过程,这一花茎是他从前往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代表团成员那里获得的。 今天,绵枣儿在早春时节会布满北方的花园,犹如一条鲜蓝色的地毯。
百合是否为西欧土生土长的花朵至今未明,但是毫无疑问,原产地为巴尔干半岛和西亚的白百合(圣母百合)可追溯到久远的古典时期。 正如百合的名称所指,它能让人联想到纯洁和美德,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
其他百合品种则来自君士但丁堡。 壮丽的皇冠贝母(冠花贝母)的原产地从库尔德斯坦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麓下,其中红色的花朵通常被当地人用作染料。 它是无数传说的主题,也是微型画和刺绣品中常见的图案。 1576年克卢修斯获得了从奥斯曼帝国转送到维也纳的花茎,不久之后,这种花就成为了典雅花园的“必备花”,不过如今它的种植范围相对有所缩减。 黄色品种的一品黄在1665年首次被提及。
十六世纪引入(可能沿同一路线)的另一品种是土耳其的头巾百合,也就是欧洲百合。 它遍布整个欧亚大陆,但是对于欧洲的某些地区是否也是它的原产地仍有一些争议。 Martagan一词在土耳其语中意指一种紧紧裹在头上的小头巾,由此可以看出,不管它是否生长在欧洲,它都是从奥斯曼世界传到欧洲的。 这个词在十六世纪出现在英语中,而到1597年即已有明确的史料提及它生长在挪威的卑尔根,由此可以看出流行植物的传播速度有多么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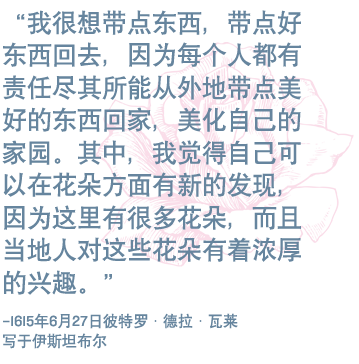 丁香(紫丁香)是整个北欧的另一种标志性春季花卉。它原产于巴尔干半岛,但是由于宗教和政治分歧,它分别通过两个方向从君士但丁堡的花园传到西欧: 德·巴斯拜克将其带到了维也纳,同时威尼斯大使将其引入了意大利。
丁香(紫丁香)是整个北欧的另一种标志性春季花卉。它原产于巴尔干半岛,但是由于宗教和政治分歧,它分别通过两个方向从君士但丁堡的花园传到西欧: 德·巴斯拜克将其带到了维也纳,同时威尼斯大使将其引入了意大利。
英国驻莫卧儿和奥斯曼王朝的大使托马斯·罗欧爵士(Sir Thomas Roe),在十七世纪初期应约翰·特雷德斯坎特的要求,将多种植物带回了家乡;约翰·特雷德斯坎特是多名贵族成员的园丁主管,包括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和查理一世。
在这一时期,人们为了用最不同寻常的植物装点出最好的花园互相攀比,愈演愈烈。 白金汉就吩咐过黎凡特的商人竭尽全力为自己搜罗外国的奇异花朵。 因此,特雷德斯坎特奉命前往荷兰,并从那里引入多种来自中东的植物实属正常之举。 他还曾远征俄国,并从那里带回了新物种,包括落叶松以及一种香味非常浓郁的石竹。 (可悲的是,特雷德斯坎特自己无法亲身验证: 他闻不到气味。)
在欧洲,石竹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们出现在许多绘画以及手稿页边中,不过通常以五瓣小平花的形象出现。 奥斯曼人所钟爱的多褶康乃馨显然与之不同,几乎肯定是由后天培育而成的;它们没有野生原种,因此可能是地中海麝香石竹的杂交品种。 这些石竹在十六世纪中期从君士但丁堡传到英格兰,其特征是重瓣,绯红色,与丁香花的香味相似。
 |
| 私人藏品/卡洛琳·斯通 |
| 这部波斯诗集插图册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早期;从这一页中可以看到水果花、紫罗兰和绵枣儿散布其中,中间位置是大马士革蔷薇。 |
部分康乃馨的繁育是从奥斯曼花园和西方开始的。 到十七世纪早期,康乃馨的品种已达几十种,某本英语名录提到了63种,而土耳其的《康乃馨论著》(Karanfil Risalesi)则用插图进行展示,其中某些品种为今天世界上出售范围最广泛的现代康乃馨提供了原种。
为了借机去更远的地方旅行,1620年特雷德斯坎特自愿出征讨伐阿尔及尔海盗。 远征并没有获胜,但是他成功在摩洛哥得土安附近登岸,并记述“他看到了巴巴利数公顷的土地上布满了Corne Flagge(即剑兰)。” 即使到二十世纪后期,紫红色的土耳其剑兰花田在北非也堪称壮丽景色。
剑兰家族大部分生长在撒哈拉南部,不过比较适合北部环境的品种迅速流行起来,而这一品种也是今天大多数花园剑兰的原种。 奇怪的是,伊斯兰世界的园艺家和艺术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它,这可能是因为它与花园的关联不大,反而与农业大有关联——人们将其当作杂草铲除! 此次远征的其他战利品包括在当时优于英格兰杏树的品种“阿尔及尔杏树”,以及“色泽呈极亮绯红色,与柔软康乃馨颜色类似”的野生石榴(其培育品种是已知的),特雷德斯坎特这样写道。
在这一时期,所有这些来自东方的植物都漂洋过海,跟随魄力非凡的园艺家们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和南美,逐渐适应那里的环境,并传到更远的西方。 到十八世纪中期,傲立于君士但丁堡、阿勒波、维也纳和莱顿等地花园中的花朵逐渐成为亚历山大、弗吉尼亚及附近的乔治城中常见的花朵。
 |
卡洛琳·斯通(stonelunde@hotmail.com)往来于剑桥和塞维利亚两地。 她与保罗·兰德(Paul Lunde)一起翻译的新作《伊本·法德兰与黑暗之地》(Ibn Fadlan and the Land of Darkness)搜罗了远北地区中世纪的阿拉伯传闻,在2011年由“企鹅经典”出版。 |